作者简介:张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何雪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蔡志楠,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威廉·洪堡是德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参与了柏林大学的创建工作,他与柏林大学的关系在其身后常被误传,他对德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也有被夸大之嫌。由此形成了洪堡神话并衍生出柏林大学获得成功的“柏林模式”。近些年来,德语学界的历史学家们展开了针对洪堡以及柏林大学早期校史的质疑与批判,层层解构了洪堡在德国现代大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梳理和反思解构的内容与过程之后人们将会发现,德国学者反复纠结于洪堡神话,乃是对德国大学前景的担忧所致。
关 键 词:洪堡神话 柏林大学 大学理想型 研究型大学
标题注释: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大学的历史变迁研究”(批准号:18BSS004)资助。
中图分类号:G5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8)03-0132-16
一、洪堡神话:洪堡的大学思想与柏林大学的创建
凡论及德国现代大学史,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一位必然要被提及的人物。①一般认为,是洪堡主导了柏林大学的创建,堪称“柏林大学之父(Vater der Berliner  )”。②1810年初创的柏林大学在洪堡所提倡的教育与研究合一、教学自由的精神引导下大获成功,遂成典范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效仿对象。④在柏林大学的示范作用下,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末普遍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然而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不断有学者对上述认知提出质疑。近些年来,诸多扎实的史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认为,洪堡大学思想的引领、柏林大学堪称典范等一系列观念乃是误识,应归为“神话(Mythos)”。⑤因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现洪堡大学思想主旨的重要文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②1810年初创的柏林大学在洪堡所提倡的教育与研究合一、教学自由的精神引导下大获成功,遂成典范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效仿对象。④在柏林大学的示范作用下,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末普遍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然而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不断有学者对上述认知提出质疑。近些年来,诸多扎实的史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认为,洪堡大学思想的引领、柏林大学堪称典范等一系列观念乃是误识,应归为“神话(Mythos)”。⑤因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现洪堡大学思想主旨的重要文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die innere und
die innere und  Organisation der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在洪堡生前并未获得发表,甚至在整个19世纪都不为人所知。在此前提之下,当代德国的多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认为,现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原则并非出自洪堡的大学思想,而是在洪堡身后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史中,洪堡及其大学思想的作用、柏林大学的历史地位等,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上述误识乃是20世纪的臆造。学界将此臆想称为“洪堡神话(Mythos Humboldt)”⑥,或者“洪堡式大学神话(Mythos der Humbold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在洪堡生前并未获得发表,甚至在整个19世纪都不为人所知。在此前提之下,当代德国的多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认为,现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原则并非出自洪堡的大学思想,而是在洪堡身后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史中,洪堡及其大学思想的作用、柏林大学的历史地位等,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上述误识乃是20世纪的臆造。学界将此臆想称为“洪堡神话(Mythos Humboldt)”⑥,或者“洪堡式大学神话(Mythos der Humboldtschen  )”⑦。
)”⑦。
为使国内学界更透彻地了解针对洪堡神话的域外讨论,本文将率先梳理出洪堡与德国现代大学史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德国历史学家群体逐步解构的,以此补充知识考古式的研究⑧。如下几则事实构成了本文的讨论基础。
第一,19世纪末期,著名的德国史编纂家布鲁诺·格布哈特(Brurio Gebhardt,1858~1905)在研究洪堡生平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洪堡未曾发表的、没有完成的,甚至未注明撰写日期的手稿,题为《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1896年,格布哈特公布了该手稿的部分内容,马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1900年,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在为柏林科学院撰写的史志中引述了洪堡在文中所表达的思想。⑨随后,格布哈特在1903年出版的《洪堡全集》中将该文全篇刊发。⑩从此,洪堡在文中树立的大学理想型被广泛引用。(11)其中的核心内容包括(12):大学“总是把学术视为尚未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或者说“科学是一个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问题,当锲而不舍地探索之”,而大学“与任何政府机构无关”,“寂寞与自由(Einsamkeit und Freiheit)”是它的“支配性原则”等。(13)
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洪堡的这篇文稿写于1809年~1810年。此时的洪堡担任普鲁士王国的文教司长,正着手普鲁士教育体系的改革工作。他论及教育与学校的其他著名篇章如《柯尼斯堡学校计划》(Der  Schulplan)、《立陶宛学校计划》(Der Litanische Schulplan)、《文化教育司报告》(Bericht der Sektion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等,都是在这一年多之内集中完成的。而就在同时,柏林大学也正处于创建前紧锣密鼓的筹备期,该项工作属于洪堡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洪堡在这一时期写下自己对大学的思考,符合文献产生的历史时间和事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Schulplan)、《立陶宛学校计划》(Der Litanische Schulplan)、《文化教育司报告》(Bericht der Sektion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等,都是在这一年多之内集中完成的。而就在同时,柏林大学也正处于创建前紧锣密鼓的筹备期,该项工作属于洪堡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洪堡在这一时期写下自己对大学的思考,符合文献产生的历史时间和事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二,为了充分而全面地理解洪堡的大学思想,不仅需要分析《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还必须结合《柯尼斯堡学校计划》《立陶宛学校计划》《文化教育司报告》等一系列与教育相关的文论。(14)综合视之,洪堡思想中的大学集研究和教育两项职责为一身。大学不但发展学术也培养人才,对人才的培养应在参与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学术可以修养个性、完善人格,通识教育和自我教育因此尤为重要。所以,大学不能办成专科学校,也不直接服务于政府的实际需要,而是要独立于政府——但政府需为大学的繁荣创造条件和保障。大学的师生应甘于寂寞、潜心学术,自由地进行学术的探索。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作为具有研究性质的高等学术机构应为此提供适宜的环境。另外,大学与科学院都是高等学术机构,两者之间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它们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必要。两者可以拥有部分共同的成员,科学院的院士都可以来大学讲课。大学可以将系列的观察和实验委托给科学院去完成。而大学自己追求的应是纯学术(Wissenschaft),其基础是哲学。简而言之,教研合一、教学自由、大学独立是洪堡大学思想中的核心内涵。(15)
在洪堡的大学思想中含有很多浪漫主义的乃至理想主义的成分,例如大学独立于政府、师生只追求纯学术等。所以,洪堡所勾勒出的大学模式难免被形容为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学界已注意到在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与19世纪德国大学的实践之间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差异。(16)但是,由于在洪堡主政期间,柏林大学得以成功创建,人们难免错误地将此殊荣归功于洪堡,也错误地将柏林大学打上了洪堡式大学的标签。史实不清乃是臆造洪堡神话的原因之一。
第三,洪堡本人并不是柏林大学的创建人,更未曾担任过柏林大学的校长。1809年2月,作为普鲁士王国驻罗马外交官的洪堡接受了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任命,成为普鲁士内政部(Ministerium des Inneren)负责文化与教育部门的主管(Direktor der Sektion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相当于文教司长。这其实是洪堡本人并不愿意接受的职位,但是王命难违,洪堡只能回柏林就职。(17)自此,洪堡开启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小学、中学、大学三级连贯的学校体系。然而在16个月之后,即1810年6月,洪堡主动请辞并获得批准。(18)随即,洪堡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外交官并于同年9月赴任。之后,柏林大学于1810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是法学家特奥多尔·施马尔茨(Theodor Schmalz)。
其实早在1808年末,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神学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等知名教授已经开始在柏林开堂授课。其背景原因是普法战争爆发之后,普军的失利使各地的学者纷纷避居柏林,特别是一批来自被拿破仑关闭的哈勒大学(时名Friedrichs- Halle)的流亡教授,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古典学家沃尔夫等知名学者。这批教授从1807年起开始倡议,在柏林新建一所大学,弥补普鲁士王国失去哈勒大学的损失。
Halle)的流亡教授,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古典学家沃尔夫等知名学者。这批教授从1807年起开始倡议,在柏林新建一所大学,弥补普鲁士王国失去哈勒大学的损失。
洪堡实际上只经历了柏林大学1809年~1810年最后的创建筹备阶段。(19)即便如此,四卷本《欧洲大学史》的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üegg)仍然认为,洪堡为柏林大学的成功创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原因在于,是洪堡说服了普王放弃仿效法国建立专科学校的念头。原来,拿破仑上台之后关闭了法国的传统大学(université),改设各种独立学院(facultés professionnelles)和专科学校(écoles spéciales),培养以职业为导向的专门人才,从而确立了19世纪法国高等教育的模式。1806年10月,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大败普军,随后关闭了德意志大学在当时的“旗舰”——哈勒大学。是月,法军进入柏林,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被迫割地赔款。但普鲁士王国知耻而后勇,开启了国家的全方位改革,其中包括大力兴办教育,用普王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Der Staat muss durch geistige  ersetzen,waser an physischen verloren hat)”。然而,普王最初的考虑是仿效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柏林设立高级专科学校。学界也不乏对普王的附和之音。在普王还未做出决策之时,洪堡通过行使文教司长的职责,于1809年7月24日正式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主张在柏林以大学的形式新建一所高等学术机构。(21)洪堡的进谏获得了成功,普王改变决心并最终在1809年8月16日颁布内阁敕令,在柏林创建一所新的大学(
ersetzen,waser an physischen verloren hat)”。然而,普王最初的考虑是仿效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柏林设立高级专科学校。学界也不乏对普王的附和之音。在普王还未做出决策之时,洪堡通过行使文教司长的职责,于1809年7月24日正式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主张在柏林以大学的形式新建一所高等学术机构。(21)洪堡的进谏获得了成功,普王改变决心并最终在1809年8月16日颁布内阁敕令,在柏林创建一所新的大学( 。(22)正是在洪堡的极力劝谏之下,柏林大学的创建才成为可能,他是在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23)
。(22)正是在洪堡的极力劝谏之下,柏林大学的创建才成为可能,他是在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23)
虽然,威廉·洪堡作为幕后推手在促成柏林大学创建的事业上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他担任文教司长的时间不过一年有余,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彻底颠覆时人对大学的认知和对专科学校的青睐。在1810年前后,功利主义依然主导着当政者兴办高等学校的观念。而且,德意志的时局也亟须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级人才立刻承担起复兴国家的重任。问题是,创建之初的柏林大学是否在按照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办学呢?事实并非如此。1810年的柏林大学未能彻底地除旧布新,而是继续保留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架构,设置了文学、医学、法学、神学四大学部,统领各个学科分支。从办学模式上来看,德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开端是在哈勒和哥廷根(24),柏林大学却未见得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
二、成功的德国大学模式:与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渐行渐远
不可否认的是,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大学建立起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体系,以研究为导向的教研结合已经成为德国大学的标签。在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医学等研究领域,德国的大学一骑绝尘,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以至于在很多专业领域,德语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语言,大量的学术期刊都以德语为出版语言。从1901年至二战爆发之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也以说德语的学者居多。1900年前后的德国大学模式不但获得了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更被英、美等西方强国的大学奉为仿效的榜样,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末无疑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先行者和引路人。
由此,柏林洪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吕迪格·冯·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认为,1900年应该作为德国大学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德国大学在当时的状态与19世纪之前的大学已截然不同。但问题是,1900年前后的德国大学是否因实践了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才获得成功呢?布鲁赫教授的考察结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25)
布鲁赫归纳出洪堡式大学理想型的四个维度:第一,大学相对于政府具有绝对的独立性;第二,各类学术(Wissenschaften)是一个统一的整体(Einheit),其最根本的基础是哲学;第三,大学教育通过学术的训练提供塑造人格的机会;第四,学术是为了追求新知,大学不能仅传授既有知识,政府要为此提供持续的制度保障,而大学中的学者所享有的是“寂寞与自由”。布鲁赫承认,尽管1900年前后的德国大学取得了公认的不菲成就,但若以上述的标准逐条考查,当时的德国大学——也包括柏林大学在内——与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还相差甚远。洪堡大学思想中的某些标准即便进入了办学实践当中,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了折扣或者是妥协后的结果。更不用说《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时至1903年才首次全文公开,在此之后又被片面地引用。布鲁赫在此处所指,正是上文提及的哈纳克在1909年11月21日的一篇旨在成立新的研究型学会的演讲中,援引洪堡此文为自己立论。哈纳克认为,研究型学会就是洪堡在文中提及的在大学和科学院之外的辅助机构,学会的意义在于将研究工作从大学分离出来而独立进行。(26)而哈纳克是当时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二世特别倚重的私人顾问,国家的学术政策深受哈纳克的影响。(27)布鲁赫通过考察19至20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的学术政策发现,当时德国的政界与学界对科技研发的偏爱显而易见。例如以威廉皇帝命名的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实体机构“威廉皇家学术促进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der Wissenschaften)”——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前身(1948年改名)——在1911年1月11日正式成立,哈纳克本人担任首任会长达20年之久。在二战爆发之前,威廉皇帝学会吸引来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学者,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出类拔萃,共诞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1921年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爱因斯坦。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专门从事研究的学会与洪堡大学思想中教研合一的原则背道而驰。
der Wissenschaften)”——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前身(1948年改名)——在1911年1月11日正式成立,哈纳克本人担任首任会长达20年之久。在二战爆发之前,威廉皇帝学会吸引来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学者,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出类拔萃,共诞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1921年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爱因斯坦。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专门从事研究的学会与洪堡大学思想中教研合一的原则背道而驰。
布鲁赫还指出,在1900年左右的德国大学里,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联系正在被打破,因为将两者相结合的做法在实践当中有时会降低研发科技的效率,与国家和政府对科技进步速度的期望不能相符。随着当时工业化导致的社会需求,技术高校(Technische Hochschule)引领了科技研发的方向,而传统大学( )里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倒向实际生产的需要。这无疑与洪堡期望大学追求纯学术的思想相悖。在教学方面,专科学校例如商业高校(Handelshochschule)提供的实用性知识越来越受到更多青年学子的青睐,进而在此类高校中诞生了新的资质,例如经济学文凭(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s Diplom)等。另外,1900年前后正是学术巨擘大量在德国的大学中出现的时期,由此在大学的学者之间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学术身份等级,这与洪堡提倡的教师与学生建立平等学风的思想也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各级政府在对新建的大学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师生们“寂寞与自由”的状态根本无法获得保障。
)里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倒向实际生产的需要。这无疑与洪堡期望大学追求纯学术的思想相悖。在教学方面,专科学校例如商业高校(Handelshochschule)提供的实用性知识越来越受到更多青年学子的青睐,进而在此类高校中诞生了新的资质,例如经济学文凭(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s Diplom)等。另外,1900年前后正是学术巨擘大量在德国的大学中出现的时期,由此在大学的学者之间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学术身份等级,这与洪堡提倡的教师与学生建立平等学风的思想也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各级政府在对新建的大学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师生们“寂寞与自由”的状态根本无法获得保障。
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大学与洪堡式大学理想型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大学所造成的伤害无法估量。尽管在一战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学的研究工作再次经历短暂的春天,但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实行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是对教学自由理念的釜底抽薪。纳粹政权将大学完全束缚在畸形的意识形态之下,个别学科甚至沦为纳粹的传声筒,这给1933年~1945年的德国大学史涂上了阴暗的褐色。所以布鲁赫认为,德国大学的黄金时代终于20世纪30年代。
总之,在布鲁赫看来,德国的大学在1900年前后获得的成功以及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复兴,都不是洪堡的大学思想在起作用,而是德国大学在自身发展中逐步取得的成就,其实践原则更多地吸收了施莱尔马赫的大学思想,即以系、研究所、实验室构成大学的基本框架而建立自治的、学科健全的研究型大学。其中既有纯粹哲学思想的引领,也满足了实用主义的需求。
三、“柏林模式”也是神话
洪堡神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自进入20世纪以来,洪堡式大学几乎成为德国大学的标签。人们曾经认为,洪堡是柏林大学办学方针的主导者,或者说柏林大学自1810年创建伊始采用的就是洪堡勾勒的理想型大学模式。进而认为,由此形成的“柏林模式(Berliner Modell)”确立了柏林大学的榜样地位,被19世纪德意志各地的大学奉为效仿的对象。于是,柏林模式成为洪堡神话中的一部分,柏林大学也几乎成为洪堡式大学理想型的代名词。
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学教授西维娅·帕勒切克(Sylvia Paletschek)的研究却表明,所谓的柏林模式也是不存在的,一样应当予以破除。(28)她遍查19世纪编纂的教育史著作以及各种百科全书类的辞书后发现,在当时人们对大学的理解和定义中,根本没有教研合一的特性;在办学原则方面,时人既没有提及洪堡,也没有将柏林大学奉为圭臬。帕勒切克分析认为,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诸多邦国意识到自己的大学在衰落,必须进行改革。1790年~1830年,德意志各邦国——当然也包括普鲁士——纷纷开启了大学改革。结果是,一方面大学对政府的财政依赖越来越强,逐渐失去社团自治的身份和特权,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大学因此承担的重要职责是培养未来的政府官员。另一方面,当时德意志各邦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使得邦国之间进行全方位的竞争,这也促成了大学之间形成良性的竞争关系。具体的表现是,大学越来越注重对研究的创新和突破,以此彰显各自的实力和水平。在此过程中,为每个学科专门设立系、研究所、实验室的模式,在各所德意志大学里面逐渐普及起来。这一举措乃是德意志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典范之举,在后来被其他国家的大学纷纷效法。此乃德意志大学的总体转向,并非柏林大学一校之功。此外,德意志大学获得成功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教授的严格选拔,杜绝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1800年左右,哈勒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已开始实施编外讲师制度(Privatdozentur),从已获得从教资质的学者中间遴选高水平的教授。而教授资格(Habilitation)则于1870年~1880年在德国各大学通行起来,它是学者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对自己研究能力有所提高的再度展示。进入20世纪之后,大学对教授资格论文实行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在以上这些对19世纪的德意志大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方面,柏林大学均未曾率先垂范。帕勒切克在考察了柏林大学首部《大学章程》于1816年的初稿后发现,官方在当时的基调以及柏林大学自身的定位都不想让柏林大学标新立异,而是“与所有德意志的大学拥有同样的目标……与(普鲁士)王国内的其他大学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在经济来源方面,柏林大学完全依靠政府,这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各邦国的大学经过改革后的地位并无不同。所以,像其他任何一所德意志大学一样,创建之初的柏林大学根本无法相对于政府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整个19世纪是德意志大学集体经历改革和转型的时期,但是柏林大学并不是当时的改革焦点。相反,一系列的事实表明,柏林大学即使在创建之后也没有急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而是逐步接受了其他德意志大学于1790年~1830年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例如柏林大学在开学两年之后即1812年,才开设了第一个研讨班(Seminar),主持者是施莱尔马赫。而史学大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主持的研讨班直至1830年还只是他的私人课堂。在遴选教授的事务上,柏林大学受到普鲁士文教部门的干预,这对大学自主选拔教师是很大的限制。当然,帕勒切克也认为,新建的柏林大学并非一无是处。它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受到普鲁士王室的直接支持,地处王国的首府也使得柏林大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吸引足够的师资和生源,一举创建成功。但就吸引师资来看,洪堡却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因为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沃尔夫等知名教授在1807年就已经齐聚柏林。而洪堡计划从外地延聘到柏林大学就职的教授,大多在1810年开学之际拒绝了聘任。
帕勒切克还指出,柏林大学的特殊地位是其他德意志大学根本无法比拟的,这也使柏林大学不可能成为仿效的对象。柏林大学能从普鲁士政府获得充足的经费来源,资助随着普鲁士王国的日益强大还在不断提高,中小邦国的大学则望尘莫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以后,柏林大学以地利之便成为新帝国的标志之一,更获得了帝国政府财政支持的倾斜,其开销的83%来自政府拨款。反观被纳入帝国版图的其他德意志大学的经费来源,平均只有63%来自帝国政府。同时,柏林作为国家首府,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在创建大学之前已经拥有科学院、图书馆、博物馆、医院以及各种专业收藏,它们可以与柏林大学相互补充和协作。但大多数其他德意志大学位于中小城镇当中,无法具备上述的条件。
既然柏林大学在整个19世纪并没有被其他德意志大学作为楷模去仿效,为什么会出现柏林大学乃洪堡式大学榜样的误识呢?帕勒切克认为,洪堡神话是20世纪人的臆想,其形成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一文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洪堡的大学思想对研究工作尤为看重,而当时德国大学的成功之处恰在于科研方面的绝对领先。这难免令人展开联想,认为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就已然如此。其次,1910年正逢柏林大学的百年校庆,喜悦使时人冲昏了头脑,特别是当时在柏林大学任教的部分教师,在整理柏林大学百年历程的过程中,夸大了洪堡大学思想的作用。(29)再次,在19至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飞速发展,其强劲的势头已非传统的人文学科可比,所以当时的一些大学学者需要用新人文主义的大学思想鼓舞自己,为人文学科增值,而洪堡的大学思想恰好具有新人文主义的鲜明特性。最后,在同一时期,德国大学的成功模式蜚声世界,出于提高国家政治影响力和民族地位的目的,一些学者(大多不是历史学家)刻意美化德国的大学,将其臆造为洪堡式的大学。
帕勒切克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认为,臆想出来的洪堡式大学神话在20世纪被不断地重复,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一次臆造都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错误认知的印象。(30)
第一个阶段在1900年~1910年,是洪堡式大学神话的形成期。当时的普鲁士人认为,伟人与思想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柏林大学的成功是普鲁士精神的集中表现,伟人就是洪堡,思想就是新人文主义。所以,洪堡神话的形成其背后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在给予支撑。有了洪堡的大学思想作为光环,可以掩盖柏林大学享受官方优待的特殊性,使得德国的大学和学术蜚声世界看上去完全是大学自身努力的结果。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德国人认为当时的处境与一百多年前普鲁士败给拿破仑有相似之处,教育的不足对战争的失败应承担部分责任。魏玛共和国的主政者为了保持19世纪德国大学开创的领先局面,坚持推行教研合一,希望通过对洪堡大学思想的唤醒,树立起大学的理想型而强调大学的非功利性,重申大学教育不是职业教育,是对人格的塑造,大学进行的学术与理论教育优于技术与实践。其背后的政治意图是,效仿普鲁士王国复兴过程中创建柏林大学的举措,通过对理想型大学的塑造重新振作民族精神。
第三个阶段是1933年~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纳粹政府想把大学改造为培养政党和国家未来领导者的工具,但同时也要坚持科研工作,所以认同通过学术研究进行大学教育的观念,并鼓吹学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大学的理想型被纳粹拿来作为建设政治化大学(politische  )的宣传工具。
)的宣传工具。
第四个阶段是二战之后。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而双方都试图唤回洪堡的大学思想和新人文主义精神。东德一方认为,洪堡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是大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指路人,于是在1948年干脆将柏林大学更名为洪堡大学。(31)西德方面希望通过重树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新人文主义思想、古典主义精神,来清除纳粹的思想残余,接续纳粹之前的优良传统。所以在战后不久,西德的学者纷纷祭出理想型大学的愿景。例如卡尔·特奥多尔·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认为,大学不能沦为专业学院,只有当学术领域被重新树立起来了,学术性和人性才有保障,大学应是一个大而全的整体;尽管有系科的划分,考察和科研工作还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32)二战后的洪堡神话不单有助于杜绝培养野蛮人,还可以将在洪堡式大学理想型中体现的民主传统与德国自身的历史结合起来,从而说明,纳粹时期是在延续传统过程中的突然中断。
四、德国大学的自我审视
以上的研究是从大学外部入手解构洪堡神话。那么德国大学如何看待自身的成功历程呢?图宾根大学历史学教授迪特尔·朗格维舍(Dieter Langewiesche)以独特的视角选取了一批代表大学自身观点的史料来回答上述问题。他专门搜集和研究了自1871年德国统一后的百余年间,各所德国大学校长每年一度的公开演讲,以此来透视大学的自我审视,因为大学校长基本都是教授出身,是大学当中教研活动的亲身参与者。同时,作为一所大学的掌舵人,校长把握着各自大学的办学原则,最了解大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德国大学校长公开演讲的内容,既包括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研究进展,也会谈及大学的总体情况,同时会讨论教育和学术政策,足以反映德国大学自身的立场。
朗格维舍的研究认为,洪堡神话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现如今常被当作误识的思维定式。(33)在19世纪的大学校长演讲当中,根本没人提及过洪堡的大名,也没有校长谈及以柏林大学为榜样;1945年之后的演讲开始对洪堡有所涉及,20世纪70年代逐渐增多,而提到洪堡以及洪堡模式最多的就是柏林大学的历任校长。在19世纪德国大学校长演讲中所能体现的共识是,德国大学的办学实践是以研究为先,在研究之上建立教学,教育是通过作为研究者的教师实施的,研究、教育、学习都应享有广泛的自由度。大学校长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大学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而不仅仅是普鲁士的功劳。大学本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基础之一,是德意志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很多校长看来,引导各自大学前行的并不是邦国的王侯们,而是民族观念形成的精神动力。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获得的空前成功,是德意志民族结为统一的整体之后在文化方面的第一个结晶。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以联邦为基本原则的德意志民族历史观,是与以某所精英大学为效仿蓝本截然相反的大学史观,而后者所指正是洪堡神话中的“柏林模式”。
朗格维舍认同帕勒切克的观点和分析,认为对洪堡式大学神话的臆造发生在20世纪早期,这在当时柏林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有充分的表达。(34)他们在演讲中勾勒出了理想型的大学:永远是真理的源泉,永远向真知敞开着大门,是塑造人格的地方,也是培养精英和领袖阶层的地方,大学是能将思想中的理想型变成现实的地方。他们让听众认为,这样的大学就是洪堡式大学,而洪堡又与柏林大学的创建分割不开。所以,20世纪初的柏林大学自身也助长了洪堡神话的形成。朗格维舍指出,德国大学的共有特点之一是与政治和时局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在柏林大学身上的反映最为明显。柏林大学创建的历史背景以及地处首府的优越位置,使它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乃至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寄托。在此,朗格维舍引用了19世纪末柏林大学教授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的观点(35),即柏林大学犹如普鲁士王国重新崛起的长子,但是从学术上看它并不优于其他的德意志大学。但在蒙森看来,普鲁士王国能够成功统一德意志、领导构建民族国家,背后有三根重要支柱,即军事体系、经济实力、精神动力,而柏林大学正是精神动力的突出代表。
朗格维舍指出,德国大学的校长们将大学刻画为现代性的实验室(Laboratorium der Moderne),它是教育的场所,也是进步的保障和动力,人们在里面学习的是常新的精神。不仅如此,大学还可以塑造社会、国家和民族。在近代德国史上,曾经出现过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获得胜利的神话、普鲁士崛起的神话。这两者与洪堡神话(或者叫作洪堡式大学神话、“柏林模式”神话)一同构成了近代德意志的民族神话和国家神话。
五、小结、思考与展望
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群体通过层层解构力图戳破洪堡神话,还原德国大学于近现代崛起的真相。在此过程之中,上述几位学者充分展示了以史学方法探究教育问题的方式,即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对史实的严谨重构,由此澄清洪堡神话背后的历史原貌。历史表明,现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原则是在洪堡身后逐渐形成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当中均不存在洪堡式的大学,它是理想型大学的一种模式,而柏林大学的“洪堡式”标签更是被后人附加上的。德国大学在19至20世纪所获得的成功并不是遵照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按图索骥,而是各所大学纷纷积极改革、创新实践的集体结晶,柏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只是德国大学近代改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36)诚然,在1900年前后德国大学成功崛起的因素当中,不乏与洪堡大学思想中的某些理念相契合的成分。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至今仍是一项未能完全付诸实践的挑战。洪堡神话恰恰说明洪堡大学思想的重要性,它对于过往和今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设定为大学锐意进取的未来目标并努力实践之,正是洪堡的大学思想具有持久价值的现实体现。(37)而柏林大学即便未曾作为德国大学的楷模,其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当前进行的“双一流”建设依然具有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38)
当然,这并不是说洪堡的大学思想本身没有缺憾。例如洪堡自己未曾有过大学的执教经历,他关注的焦点更多停留在办学原则的宏观层面,又过于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他无法预测现代社会中的大学生若缺乏实用性的知识在就业时面临的困境。而且,洪堡的大学思想必然会受到时代局限性的阻碍,他本人没能经历科学与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迅速分化而从哲学学院独立出来建立学系、实验室,都有悖于洪堡的大学思想中以哲学统领所有学科的学术理念。不过,所有这些业已是洪堡的身后之事。(39)
如此看来,洪堡的大学思想似乎已无法适应现代大学的要求。既然如此,当代德国历史学家群体为什么在近年来热衷于钩沉洪堡神话呢?
首先,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是考镜源流,包括厘清洪堡的大学思想、柏林大学的创建、德意志大学的总体改革等史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其中的来龙去脉,分析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对洪堡神话的反复臆造和传颂,不仅仅出于德国大学自身改革的需求;每次臆造均与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直接相关,都需要祭出洪堡这个标签。(40)创建和兴办大学——起码在德国——从来就不单纯是高等教育界内部的事务。洪堡神话以及附属的柏林大学神话,与德国近代的政治历史、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相连。所以,对德国大学史的研究远超出教育史的范畴,它已上升到国家层面,曾经是德国走向发达国家进程中的辉煌一页。(41)也正因为如此,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尤为关注德国大学的历史。虽然有关洪堡神话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德国的历史学家们率先表现出了反躬自省的态度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其次,破除神话的努力反映出德国历史学家们的现实关怀与忧虑。(42)德国的大学在二战之后直至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经过二战之后20余年的重建,20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经济复兴、社会稳定、人口增加,使得大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陡然而至,对提高大学质量的期望也与日俱增。突然增高的入学率使大学生挤破了大学教室: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三十年间,西德大学生在校数量增长了十倍。虽然西德自60年代以来新建了二十余所公立大学( ),但大学数量的增加远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大学面临成为大众学府(
),但大学数量的增加远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大学面临成为大众学府( )的危机。时至20世纪80年代,各种矛盾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学生数量激增导致教学资源短缺,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的教学场所;大学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压力增大,但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对偏低,同时还要坚持科研为本;年轻学者在大学体系内立足越来越难;另外,公众对大学的期许和要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严重威胁到德国大学在近现代形成的鲜明特点,即以教研合一的模式培养研究型后备力量。
)的危机。时至20世纪80年代,各种矛盾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学生数量激增导致教学资源短缺,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的教学场所;大学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压力增大,但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对偏低,同时还要坚持科研为本;年轻学者在大学体系内立足越来越难;另外,公众对大学的期许和要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严重威胁到德国大学在近现代形成的鲜明特点,即以教研合一的模式培养研究型后备力量。
再加之英语世界的大学在20世纪下半叶以迅猛的势头超越了德国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在二战之后的迅速崛起更凸显出德国大学的式微。美国的大学办学主体较为丰富而且学校层次多种多样,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有诸多学府跻身世界级大学的殿堂。相比之下,德国绝大多数大学是公立高校——这是德国大学的传统所致,而国家却无法独自承担如此众多大学的发展需求。德国的大学为谋求新的突破唯有扬长避短,而其拥有的最大优势乃是洪堡思想。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又被反复提及,针对洪堡神话于当下德国大学的作用,破除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43)
于笔者看来,各方内心所忧虑的是,德国大学的未来是该回归洪堡,还是瓦解传统转而效仿英美?若追求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那么致力于将大学的研究性职责发挥到极致便是通途吗?为了提高德国高校的国际地位、再次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德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资助“卓越计划(Exzelleninitiative)”。(44)虽然投入了——相对于德国以往的高校经费而言——大量财力,颇具成效地激发了科研成果在获得资助的大学中的产出。(45)但是,如此巨大的投入却与教学基本无涉,未能走出教学与科研相互龃龉的悖论。同时,政府的不均等拨款也拉大了受资助大学与未受资助大学之间的差距(46),有损德国高校之间公平竞争、均衡发展的传统原则。(47)由此产生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大学(Elite- )”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最佳践行者吗?
)”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最佳践行者吗?
与此同时,德国的大学也转而效法英美大学的学制,那么“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是否是一剂缓解德国大学困境的良药呢?德国的大学从2010年开始统一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由传统的硕士—博士两级体制改为英美高校的三级学位体制——本科、硕士、博士。这种改革侧重于教学,细分本科生与研究生,在学生的层面将教学与科研相互剥离。然而,新的学制并未触及德国大学教研合一的原则以及教师们压力不减的窘境。自加入进程以来,德国的大学虽然获得了突出的成就(48),但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49)。“博洛尼亚进程”是否又是一则新的神话?(50)
最后,历史中的洪堡神话已被破除,但人们心中的洪堡神话并没有终结,针对大学未来发展的洪堡情节也没有被打破而是在继续生长,洪堡式大学的理想型依然备受憧憬,因为它被赋予了德国大学的复兴希望。正如德国人自己对其政治神话的解读:神话多出现在危机时期和转折时刻,它是一种集体性的尊严,会增强人们的信念,产生克服困难的动力。(51)上文曾提及近代德国历史中的三个神话:德意志人民反抗拿破仑获得胜利、普鲁士崛起、洪堡式大学。前两则神话已然实现。洪堡神话的传颂者也好、解构者也罢,他们聚焦的问题并不止于洪堡神话及其终结,更意图探究它为何没能实现,以及何时才能实现。
德国大学的成功之道既是教育学也是历史学命题。若反转思路看待德国历史学家们对洪堡神话的解构,毋宁说是对它的溯本清源和层层祛魅(Entzauberung),他们在解构的同时从侧面勾勒出了近代德国大学获得成功的大致因素,包括大学自身的改革、打造学科与振兴大学并举、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以及不可或缺的国家支持与介入等等,这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去深入阐发。所以,变换视角看待德国学界解构神话的现象——通过学术破除神话进而直面背后的问题,也是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做出展望。历史学家可以用自己的专业方式为现实问题寻求出路——要走出危机,就先要回到危机之前,回眸去剖析起初如何陷入了危机。洪堡则正是现代德国大学危机的历史源头。下一步的研究须先回到洪堡之前,进入18世纪甚至更早时代的大学史前现代时期,回溯前神话时代为神话的产生遗留的历史机遇。这涉及德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国家、德意志大学总体改革的原动力与措施、研究型大学在德国的起源等一系列问题。对这些历史问题的探讨和阐释,将有助于明确学科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梳理大学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客观展示德国大学从中世纪社团走向研究型学府的通途。
注 释:
①有关洪堡在教育领域的成就,可参见[英]沃森:《德国天才》(全四册),第1册,张弢、孟钟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69-172页。
②Hartmut Boockmann,Wissen und Widerstand-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erlin:Siedler,1999,S.189.
,Berlin:Siedler,1999,S.189.
③Thomas 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1800-1866,2.Auflag,München:C.H.Beck,1984,S.470-471.
④Heinz-Elmar Tenorth,"Wilhelm von Humboldts(1767-1835)  und die Reform in Berlin-eine Tradition jenseits des Mythos",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Neue Folge 1(2010),S.15-28.
und die Reform in Berlin-eine Tradition jenseits des Mythos",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Neue Folge 1(2010),S.15-28.
⑤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München:C.H.Beck,1987,Bd.I:1700-1815,S.480-485; Bd.II:1815-1845/49,S.504.
⑥Mitchell Ash(Hrsg.),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Wien:
,Wien:  Verlag,1999.
Verlag,1999.
⑦Walter Rüegg,"Der Mythos der Hurnboldtschen  ",in Matthias Krieg/Martin Rose(Hrsg.),Universitas in theologia-theologia in universitate:Festschrift für Hans Heinrich Schmid zum 60.Geburtstag,Zürich:Theologischer Verlag,1997,S.155-174.
",in Matthias Krieg/Martin Rose(Hrsg.),Universitas in theologia-theologia in universitate:Festschrift für Hans Heinrich Schmid zum 60.Geburtstag,Zürich:Theologischer Verlag,1997,S.155-174.
⑧张乐:《从“洪堡的教育观念”到“洪堡神话”—— 一个特定研究母题的系谱学分析》,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第10-46页。
⑨Adolf von Harnack,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d.1,Berlin:Reichsdruckrei,1900,S.594-597.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d.1,Berlin:Reichsdruckrei,1900,S.594-597.
⑩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Abteilung 2:Politische Denkenschriften(1802-1834),in 3  (insg.Bd.11-13),Berlin:Behr Verlag,1903-1904,S.250-260.
(insg.Bd.11-13),Berlin:Behr Verlag,1903-1904,S.250-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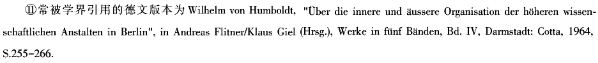
(12)根据上述五卷本德文版翻译的汉语全文见[德]弗利特纳(编):《洪堡人类学和教育理论文集》,胡嘉荔、崔延强(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98页。
(13)较早的汉译节选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本文参考2006年修订版,附录三,第197-201页。
(14)参见刘宝存:《洪堡大学理念述评》,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第63-69页。
(15)需要说明的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中有多少是自己的原创,又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他人的观念(例如施莱尔马赫),或是借鉴了其他德意志大学的改革经验(例如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和耶拿大学),乃是一个专门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上文仅是对洪堡在其著述中表达的大学思想的归纳总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大学理念是通过洪堡之名才享誉天下的。
(16)陈洪捷:《什么是洪堡的大学思想》,载《中国大学教学》,2003年第6期,第24-26页。
(17)这造成洪堡仅于在职期间保持着对大学的热忱,他主导的教育体系改革不过是恪尽职守而已。参见叶赋桂、罗燕:《大学制度变革:洪堡及其意义》,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年第5期,第21-30页。
(18)[德]康拉德:《洪堡传》,赵劲、张富馨(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3-84页。
(19)参见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载《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83-93页。
(20)[瑞士]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三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学1800-1945),张斌贤、杨克瑞、林薇等(译),张斌贤、张弛、陈露茜(审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21)Wilhelm von Humboldt,"Antrag auf Errichtung der  Berlin",in Ernst Müller(Hrsg.),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Berlin",in Ernst Müller(Hrsg.),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Leipzig:Reclam-Verlag,1990,S.267-273.
,Leipzig:Reclam-Verlag,1990,S.267-273.
(22)"Kabinettsorder  Friedrich Wilhelm III vom 16.8.1809",in Wilhelm Weischedel(Hrsg.),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Friedrich Wilhelm III vom 16.8.1809",in Wilhelm Weischedel(Hrsg.),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212-213.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212-213.
(23)[美]克拉克:《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徐震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25页。
(24)[德]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张弛、郄海霞、耿益群(译),张斌贤、张弛(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5-51页。
(25)Rüdiger vom Bruch,"Langsamer Abschied von Humboldt? Etappen deutscher  1810-1945",in Mitchell Ash(Hrsg.),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1810-1945",in Mitchell Ash(Hrsg.),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S.29-57.该文的早期版本见Rüdiger vom Bruch,"Langsamer Abschied von Humboldt? Etappen deutscher
,S.29-57.该文的早期版本见Rüdiger vom Bruch,"Langsamer Abschied von Humboldt? Etappen deutscher  im 20.Jahrhundert",Forschung und Lehre,12(1995),S.667-673;以及Rüdiger vom Bruch,"Abschied von Humboldt? Die deutsche
im 20.Jahrhundert",Forschung und Lehre,12(1995),S.667-673;以及Rüdiger vom Bruch,"Abschied von Humboldt? Die deutsch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in Karl Strobel(Hrsg.),Die deutsch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in Karl Strobel(Hrsg.),Die deutsche  im 20.Jahrhundert,Greifswald:SH-Verlag,1994,S.17-29.
im 20.Jahrhundert,Greifswald:SH-Verlag,1994,S.17-29.
(26)"Denkschrift zur Begründung von Forschungsinstituten,21.11.1909",in Wilhelm Weischedel(Hrsg.),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446-456,hier S.447.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446-456,hier S.447.
(27)Rüdiger vom Bruch,Gelehrtenpolitik,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akademische Diskurse in Deutschland im 19.und 20.Jahrhundert,Stuttgart:Franz Stein Verlag,2006,S.82-94.
(28)Sylvia Paletschek,"Verbreitete sich ein ,'Humboldtsches Modell' an den deutschen  im 19.Jahrhundert?",in Rainer Christoph Schwinges(Hrsg.),Humboldt International,Basel:Schwabe,2001,S.75-104.
im 19.Jahrhundert?",in Rainer Christoph Schwinges(Hrsg.),Humboldt International,Basel:Schwabe,2001,S.75-104.
(29)帕勒切克尤其指摘的是,当时的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斯普兰格(Eduard Spranger)对洪堡大学思想的渲染与宣扬。有关斯普兰格的著述及观点可参见张巍卓:《教化与自由——精神科学视域中的洪堡教育思想及其人性论基础》,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第47-72页。
(30)Sylvia Paletschek,"Die Erfindung der Humboltschen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10(2002),S.183-205.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10(2002),S.183-205.
(31)注意“洪堡式大学”(Humboldtsche  )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zu Berlin)在德文拼写上有区别。
zu Berlin)在德文拼写上有区别。
(32)[德]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33)Dieter Langewiesche,"Humboldt als Leitbild?",Jahrbuch für  ,14(2011),S.15-37.
,14(2011),S.15-37.
(34)Dieter Langewiesche,"Die 'Humboldtsche  ' als nationaler Mythos",Historische Zeitschrift,290(2010),S.53-91.
' als nationaler Mythos",Historische Zeitschrift,290(2010),S.53-91.
(35)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著名古典历史学家,190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6)其实柏林大学在自己的第一个百年当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沉浮与挫折,这与它深深地卷入政治时局休戚相关。可参见Charles E.McCelland,"Die  am Ende ihres ersten Jahrhunderts-Mythos Humboldt?",in Heinz-Elmar Tenorth/Charles E.McCellande(Hrsg.),Geschichte der
am Ende ihres ersten Jahrhunderts-Mythos Humboldt?",in Heinz-Elmar Tenorth/Charles E.McCellande(Hrsg.),Geschichte der  Unter den Linden.Bd.1:Gründung und Blütezeit der
Unter den Linden.Bd.1:Gründung und Blütezeit der  zu Berlin 1810-1918,Berlin: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2012,S.637-654。
zu Berlin 1810-1918,Berlin: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2012,S.637-654。
(37)陈洪捷:《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从观念到制度——兼论“洪堡神话”》,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第2-9页。
(38)参见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载《复旦教育论坛》,2010年第6期,第8-15页;张小杰:《关于柏林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的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2期,第69-77页。
(39)参见崔乃文:《回应“洪堡神话”: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组织适应机制分析》,载《复旦教育论坛》,2016年第6期,第99-105页。
(40)Martin Eichler,"Die Wahrheit des Mythos Humboldt",Historische Zeitschrift,294(2012),S.59-78.
(41)参见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42)上述几位德国历史学家在大学求学和任教阶段,都经历或见证了德国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危机——朗格维舍教授生于1943年,布鲁赫教授生于1944年,帕勒切克教授生于1957年。
(43)在2010年柏林大学创办二百周年庆典之际,国际学者们之间甚至发生了关于洪堡大学理念与现代大学实践之间矛盾的激烈论辩,参见秦琳:《洪堡模式的今日与研究型大学的明天——从〈2010洪堡备忘录〉之辩看德国大学改革》,载《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第1-6页。
(44)[英]英斯:《国际化视角下的德国“卓越计划”》,冯李崟、钟周(译),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第6-11页。
(45)朱佳妮:《追求大学科研卓越——德国“卓越计划”的实施效果与未来发展》,载《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2期,第46-53页。
(46)孙进:《由均质转向分化?——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分析》,载《比较教育研究》,2013年第8期,第1-8页。
(47)张新科、刘辕:《从均衡发展到追逐卓越——德国高等教育“卓越计划”评析》,载《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第98-102页。
(48)[德]梅尔、弗里德里希:《德国实施“博洛尼亚进程”的进展及其存在的争议》,孙琪(编译),载《比较高等教育》,2013年第8期,第88-94页。
(49)朱佳妮:《搭乘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快车?——“博洛尼亚进程”对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4年第4期,第66-74页。
(50)[德]施瑞尔:《“博洛尼亚进程”:新欧洲的“神话”?》,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2期,第91-106页。
(51)[德]明克勒:《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李维、范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页。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 收藏
收藏


 纠错
纠错 )”。②1810年初创的柏林大学在洪堡所提倡的教育与研究合一、教学自由的精神引导下大获成功,遂成典范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效仿对象。④在柏林大学的示范作用下,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末普遍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然而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不断有学者对上述认知提出质疑。近些年来,诸多扎实的史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认为,洪堡大学思想的引领、柏林大学堪称典范等一系列观念乃是误识,应归为“神话(Mythos)”。⑤因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现洪堡大学思想主旨的重要文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②1810年初创的柏林大学在洪堡所提倡的教育与研究合一、教学自由的精神引导下大获成功,遂成典范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效仿对象。④在柏林大学的示范作用下,德国的大学在19世纪末普遍转型为研究型大学。然而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不断有学者对上述认知提出质疑。近些年来,诸多扎实的史学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证认为,洪堡大学思想的引领、柏林大学堪称典范等一系列观念乃是误识,应归为“神话(Mythos)”。⑤因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体现洪堡大学思想主旨的重要文稿《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 die innere und
die innere und  Organisation der
Organisatio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在洪堡生前并未获得发表,甚至在整个19世纪都不为人所知。在此前提之下,当代德国的多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认为,现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原则并非出自洪堡的大学思想,而是在洪堡身后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史中,洪堡及其大学思想的作用、柏林大学的历史地位等,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上述误识乃是20世纪的臆造。学界将此臆想称为“洪堡神话(Mythos Humboldt)”⑥,或者“洪堡式大学神话(Mythos der Humbold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在洪堡生前并未获得发表,甚至在整个19世纪都不为人所知。在此前提之下,当代德国的多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研究认为,现代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原则并非出自洪堡的大学思想,而是在洪堡身后逐渐形成的;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史中,洪堡及其大学思想的作用、柏林大学的历史地位等,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上述误识乃是20世纪的臆造。学界将此臆想称为“洪堡神话(Mythos Humboldt)”⑥,或者“洪堡式大学神话(Mythos der Humboldtschen  )”⑦。
)”⑦。 Schulplan)、《立陶宛学校计划》(Der Litanische Schulplan)、《文化教育司报告》(Bericht der Sektion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等,都是在这一年多之内集中完成的。而就在同时,柏林大学也正处于创建前紧锣密鼓的筹备期,该项工作属于洪堡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洪堡在这一时期写下自己对大学的思考,符合文献产生的历史时间和事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Schulplan)、《立陶宛学校计划》(Der Litanische Schulplan)、《文化教育司报告》(Bericht der Sektion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等,都是在这一年多之内集中完成的。而就在同时,柏林大学也正处于创建前紧锣密鼓的筹备期,该项工作属于洪堡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洪堡在这一时期写下自己对大学的思考,符合文献产生的历史时间和事务之间的逻辑关系。 Halle)的流亡教授,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古典学家沃尔夫等知名学者。这批教授从1807年起开始倡议,在柏林新建一所大学,弥补普鲁士王国失去哈勒大学的损失。
Halle)的流亡教授,其中包括施莱尔马赫、古典学家沃尔夫等知名学者。这批教授从1807年起开始倡议,在柏林新建一所大学,弥补普鲁士王国失去哈勒大学的损失。 ersetzen,waser an physischen verloren hat)”。然而,普王最初的考虑是仿效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柏林设立高级专科学校。学界也不乏对普王的附和之音。在普王还未做出决策之时,洪堡通过行使文教司长的职责,于1809年7月24日正式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主张在柏林以大学的形式新建一所高等学术机构。(21)洪堡的进谏获得了成功,普王改变决心并最终在1809年8月16日颁布内阁敕令,在柏林创建一所新的大学(
ersetzen,waser an physischen verloren hat)”。然而,普王最初的考虑是仿效法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在柏林设立高级专科学校。学界也不乏对普王的附和之音。在普王还未做出决策之时,洪堡通过行使文教司长的职责,于1809年7月24日正式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主张在柏林以大学的形式新建一所高等学术机构。(21)洪堡的进谏获得了成功,普王改变决心并最终在1809年8月16日颁布内阁敕令,在柏林创建一所新的大学( 。(22)正是在洪堡的极力劝谏之下,柏林大学的创建才成为可能,他是在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23)
。(22)正是在洪堡的极力劝谏之下,柏林大学的创建才成为可能,他是在背后起到推动作用的“那只看得见的手”。(23) der Wissenschaften)”——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前身(1948年改名)——在1911年1月11日正式成立,哈纳克本人担任首任会长达20年之久。在二战爆发之前,威廉皇帝学会吸引来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学者,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出类拔萃,共诞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1921年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爱因斯坦。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专门从事研究的学会与洪堡大学思想中教研合一的原则背道而驰。
der Wissenschaften)”——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的前身(1948年改名)——在1911年1月11日正式成立,哈纳克本人担任首任会长达20年之久。在二战爆发之前,威廉皇帝学会吸引来大批世界级的顶尖学者,所完成的研究工作出类拔萃,共诞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包括1921年物理学奖的获得者爱因斯坦。但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专门从事研究的学会与洪堡大学思想中教研合一的原则背道而驰。 )里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倒向实际生产的需要。这无疑与洪堡期望大学追求纯学术的思想相悖。在教学方面,专科学校例如商业高校(Handelshochschule)提供的实用性知识越来越受到更多青年学子的青睐,进而在此类高校中诞生了新的资质,例如经济学文凭(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s Diplom)等。另外,1900年前后正是学术巨擘大量在德国的大学中出现的时期,由此在大学的学者之间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学术身份等级,这与洪堡提倡的教师与学生建立平等学风的思想也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各级政府在对新建的大学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师生们“寂寞与自由”的状态根本无法获得保障。
)里的研究工作也越来越倒向实际生产的需要。这无疑与洪堡期望大学追求纯学术的思想相悖。在教学方面,专科学校例如商业高校(Handelshochschule)提供的实用性知识越来越受到更多青年学子的青睐,进而在此类高校中诞生了新的资质,例如经济学文凭(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s Diplom)等。另外,1900年前后正是学术巨擘大量在德国的大学中出现的时期,由此在大学的学者之间形成了高低不同的学术身份等级,这与洪堡提倡的教师与学生建立平等学风的思想也不相符合。更不用说各级政府在对新建的大学施加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师生们“寂寞与自由”的状态根本无法获得保障。 )的宣传工具。
)的宣传工具。 ),但大学数量的增加远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大学面临成为大众学府(
),但大学数量的增加远赶不上大学生人数的增长速度。德国的大学面临成为大众学府( )的危机。时至20世纪80年代,各种矛盾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学生数量激增导致教学资源短缺,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的教学场所;大学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压力增大,但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对偏低,同时还要坚持科研为本;年轻学者在大学体系内立足越来越难;另外,公众对大学的期许和要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严重威胁到德国大学在近现代形成的鲜明特点,即以教研合一的模式培养研究型后备力量。
)的危机。时至20世纪80年代,各种矛盾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学生数量激增导致教学资源短缺,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的教学场所;大学教师们的教学工作压力增大,但获得的支持力度相对偏低,同时还要坚持科研为本;年轻学者在大学体系内立足越来越难;另外,公众对大学的期许和要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严重威胁到德国大学在近现代形成的鲜明特点,即以教研合一的模式培养研究型后备力量。 )”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最佳践行者吗?
)”是洪堡大学理念的最佳践行者吗? ,Berlin:Siedler,1999,S.189.
,Berlin:Siedler,1999,S.189. und die Reform in Berlin-eine Tradition jenseits des Mythos",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Neue Folge 1(2010),S.15-28.
und die Reform in Berlin-eine Tradition jenseits des Mythos",Zeitschrift für Germanistik,Neue Folge 1(2010),S.15-28. ,Wien:
,Wien:  Verlag,1999.
Verlag,1999. ",in Matthias Krieg/Martin Rose(Hrsg.),Universitas in theologia-theologia in universitate:Festschrift für Hans Heinrich Schmid zum 60.Geburtstag,Zürich:Theologischer Verlag,1997,S.155-174.
",in Matthias Krieg/Martin Rose(Hrsg.),Universitas in theologia-theologia in universitate:Festschrift für Hans Heinrich Schmid zum 60.Geburtstag,Zürich:Theologischer Verlag,1997,S.155-174.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d.1,Berlin:Reichsdruckrei,1900,S.594-597.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d.1,Berlin:Reichsdruckrei,1900,S.594-597. (insg.Bd.11-13),Berlin:Behr Verlag,1903-1904,S.250-260.
(insg.Bd.11-13),Berlin:Behr Verlag,1903-1904,S.250-26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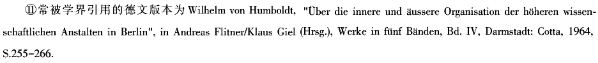
 Berlin",in Ernst Müller(Hrsg.),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Berlin",in Ernst Müller(Hrsg.),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Leipzig:Reclam-Verlag,1990,S.267-273.
,Leipzig:Reclam-Verlag,1990,S.267-273. Friedrich Wilhelm III vom 16.8.1809",in Wilhelm Weischedel(Hrsg.),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Friedrich Wilhelm III vom 16.8.1809",in Wilhelm Weischedel(Hrsg.),Idee und Wirklichkeit einer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212-213.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212-213. 1810-1945",in Mitchell Ash(Hrsg.),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1810-1945",in Mitchell Ash(Hrsg.),Mythos Humboldt: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der deutschen  ,S.29-57.该文的早期版本见Rüdiger vom Bruch,"Langsamer Abschied von Humboldt? Etappen deutscher
,S.29-57.该文的早期版本见Rüdiger vom Bruch,"Langsamer Abschied von Humboldt? Etappen deutscher  im 20.Jahrhundert",Forschung und Lehre,12(1995),S.667-673;以及Rüdiger vom Bruch,"Abschied von Humboldt? Die deutsche
im 20.Jahrhundert",Forschung und Lehre,12(1995),S.667-673;以及Rüdiger vom Bruch,"Abschied von Humboldt? Die deutsch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in Karl Strobel(Hrsg.),Die deutsche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in Karl Strobel(Hrsg.),Die deutsche  im 20.Jahrhundert,Greifswald:SH-Verlag,1994,S.17-29.
im 20.Jahrhundert,Greifswald:SH-Verlag,1994,S.17-29.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Friedrich-Wilhelms-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446-456,hier S.447.
zu Berlin,Berlin:De Gruyter,1960,S.446-456,hier S.447. im 19.Jahrhundert?",in Rainer Christoph Schwinges(Hrsg.),Humboldt International,Basel:Schwabe,2001,S.75-104.
im 19.Jahrhundert?",in Rainer Christoph Schwinges(Hrsg.),Humboldt International,Basel:Schwabe,2001,S.75-104.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10(2002),S.183-205.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10(2002),S.183-205. )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与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zu Berlin)在德文拼写上有区别。
zu Berlin)在德文拼写上有区别。 ,14(2011),S.15-37.
,14(2011),S.15-37. ' als nationaler Mythos",Historische Zeitschrift,290(2010),S.53-91.
' als nationaler Mythos",Historische Zeitschrift,290(2010),S.53-91. am Ende ihres ersten Jahrhunderts-Mythos Humboldt?",in Heinz-Elmar Tenorth/Charles E.McCellande(Hrsg.),Geschichte der
am Ende ihres ersten Jahrhunderts-Mythos Humboldt?",in Heinz-Elmar Tenorth/Charles E.McCellande(Hrsg.),Geschichte der  Unter den Linden.Bd.1:Gründung und Blütezeit der
Unter den Linden.Bd.1:Gründung und Blütezeit der  zu Berlin 1810-1918,Berlin: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2012,S.637-654。
zu Berlin 1810-1918,Berlin: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2012,S.637-654。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