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传统文化多次被知识界检讨,甚至几度遭遇全盘否定。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得到重视。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全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公众提供了“补习”的机会。然而,如何让传统文化合宜地润泽大众,如何让中国的古典文献研究与现代学术对接,仍是一个学术难题。对笔者而言,关长龙教授新著《礼学文献八讲》有一定启发,愿以“礼”和“礼学”研究为中心,浅谈现代学术与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有效对接的问题。
“礼”和“礼学”是什么?
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的遭遇,是几代人对“封建礼教”的鲜活记忆。如果我们受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为“礼学”的研究范畴就是“封建礼教”的礼,则实属认知偏颇。笔者第一次打开一本《周礼》时,就曾感到惊异:这书跟“封建礼教”的关系是什么呢?《周礼》曾名《周官》和《周官礼》,是一部记述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的专书,对官制、军制、田制、礼制等进行了全方位叙述。对标当今学科分类体系,大抵覆盖“法学大类”诸学科,即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更广。
与《周礼》相比,《礼记》《仪礼》二书谈礼仪准则和刑罚较多,与“礼教”要近一些,但内容也相当广泛,涉及朝章国典、冠昏丧祭、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等方面的具体知识。对此我们可理解为:作为西周王族政治家的周公为了塑造合格的人,在法理和法规层面对社会应有何秩序进行系统阐述,本质上是对良善治理秩序的求索。
“礼”是什么?该书给出的答案是“文化”。书中援引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理学家钱玄先生“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等论述,认为广义上的“礼”对应今日之“文化”概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看来,“礼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接近,但还不尽然。礼学广涉科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如农时节令、天文算法、相宅相墓关联的建筑工程规范等今日理工学科相关内容,都可溯源至礼学“术”之范畴;音乐、歌舞、诗赋等则更为直接地对应着上古文艺,即礼学之“乐”的范畴。总之,礼学是一个既有硬制度,又有软制度,不限于“礼节”的上古泛文化、泛制度体系。
“礼学”与现代学术的对接
在清修《四库全书总目》中,除礼学类属外,易类、书类、诗类、乐类也多与礼学相关,都属经部。“经”并非同一种类书籍的集合。礼学文献因其崇高地位,是历朝历代读书人用功最多的“科目”。自汉代以降,历朝历代都有礼学著作面世,特别是清代至为繁盛和精致。黄侃曾在《礼学略说》一文中总结:“清世礼家辈出,日趋精密,于衣服、宫室之度,冠昏、丧祭之仪,军赋、官禄之制,天文、地理之说,皆能考求古义,罗缕言之。”根据黑龙江大学康宇教授的统计,清代产出各类“三礼”文献约909种,其中《周礼》类文献252种,《仪礼》类文献225 种,《礼记》类文献249种,“通礼”类文献65种。
如何让学者迅速上手掌握浩繁的“礼学资源”?该书提供了一种可能,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礼仪、礼论、礼乐、礼器、礼法等类别,其下又继续细分。在这种结构性的分类之下,针对不同的关于“礼”的知识,重新梳理礼学文献,条分缕析地指出异同甚或承续关系,并配有各种表格,内容充实。
知识社会学关注知识的生产、积累和传播规律。而“礼学”,特别是“通礼”研究的部分,与知识社会学不无契合。如果以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来讲,必然无法将“经学”“礼学”排除在外。上溯到礼学的知识社会学,也变得更加古老。学者凭借《礼学文献八讲》这样的工具书,迅速掌握礼学纲要,锁定关键文献,进而重新理解传统礼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或许可以视作对知识社会学的反哺。
“礼学”与经验研究的对接
传统“礼学”溯及过往,而过往的方方面面又延伸至当下。将过往与当下勾连,增进对当前社会的议题理解,是礼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遵循科学范式,搁置“价值”,在礼学议题中设计更多可以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更容易实现与各学科的对接。在这一方面,部分汉学家的做法值得学习,中国学者应当提高自身在理论、方法和文献方面的综合能力。不同学科的学者要补不同的课,文史研究者可加强社会科学的训练,了解计量和统计的基本原理;社会科学的学者则要加强对经典文献的了解。象征理论、互动理论、社会建构论等社会理论,既非“硬科学”,又常常依托经验观察,因而也应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掌握。唯有在方法、理论上各自补足短板,实现学科间的“对齐”,才能最终避免学术上的“鸡同鸭讲”。
该书阐释的“礼”,其实在回答面对传统结构不断坍塌,个体渴望自主性的同时又如何克服迷茫、安顿自身的问题,这与关注工业社会到来后社会失序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学如出一辙。人类学的初衷是从异文化中找到社会最本质的规律,只不过人类学家最初踏足的是“没有文明”的社会,如今有中国这样比欧洲更有文化传统的体系做参照对比,是人类学实现进阶的好机会。
仪式是践行礼的关键部分,该书对此也着力甚多,如对“士婚礼”的理解就采用了人类学的过渡礼仪理论。既让文史学者看到人类学在仪式研究领域的成就,也向人类学学者展示了“仪礼”文献的丰富度。汉学家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是仪式研究领域的学者,其代表作《仪式理论,仪式实践》(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的原版封面就是一尊中国商代的青铜鬲,它既是烹饪器,也承担着礼器的功能,这也足见中国礼学体系在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重要性。对政治仪式的研究是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社会学、传播学的重要议题。针对个别国家国王的加冕、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游行集会和党政会议等日常政治活动,有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传统。传统中国的国家祭祀的内容,足以供政治仪式研究深挖,中国在仪式方面的系统知识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作为经学的礼学,听上去近乎一种理论研究。而事实上“礼”是经学中实践属性最强的部分。作者指出,礼经也可以理解为对“六经”的落实。该书引用《汉书·礼乐志》进行说明:“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节万事者也。”礼乐实践事关政治稳定,这不正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吗?甚至是一项干预社会的试验。
细读之下,笔者认为该书在结构安排和文风上可以优化的地方有二。首先,是作者的“松弛感”不够,对深刻的追求用力太多。在界定概念的时候,会使用对镜、境现、主体、脑体、心体、性体、道体等复杂、抽象的词汇进行解释,这就不利于读者直来直去地掌握应有的知识,而这些词汇能用简单、明晰的词汇替代。其次,礼学绵延两千年,且明清以来流派众多,外行若想了解门槛极高,如有一章能略讲礼学思想之变迁,对其他专业的读者入门礼学是很重要的。
对礼学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礼学家通常缺乏想象力,往往陷于推广礼仪、教化民众的路径依赖。这种生硬的推广,甚至形式化的表演,难免令人反感。一旦这些推广活动被大众认定为“伪道学”,又会强化公众对传统文化的排斥。让传统文化获得尊重,著书立说是最为自洽的路径。该书为读者留下了精进的空间,如果这类读物多一些,公众自然相信“祖上真的阔过”,学者和大众都能更方便地抵达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区。
(作者系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 收藏
收藏


 纠错
纠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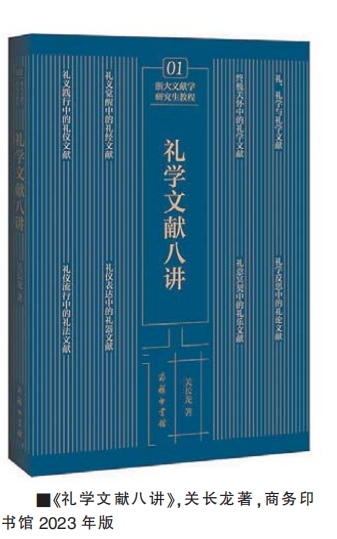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